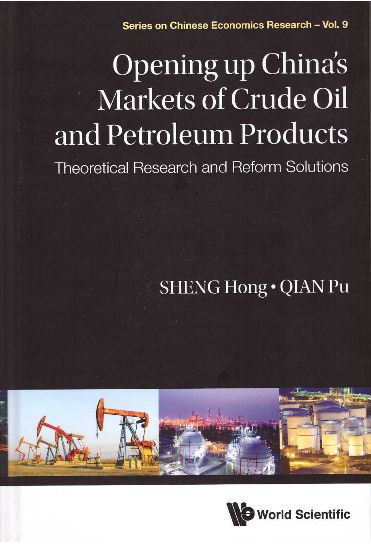张曙光:我想大家可能和我的感想一样,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太少了,今天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也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太厉害了。所以历史往往被扭曲,我们现在大概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尽管是俄国的历史,尽管是过去的情况,确实对于现实来说仍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这样,下面我们请几位专家来评论,先听听他们的高见,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好,请也夫先来讲一讲。
郑也夫:很惭愧,今天所讲的大部分内容我也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是有想象的人写的”,套用这句话,史学是呈现的不同时空下的所曾经展现出的可能性,虽然个人毫无疑问地认为,史学的贡献比文学更大,因为要呈现出前人曾经做过的多种尝试,让我们认识这种可能性曾经发生过以及它能否实现。这无疑是对今天困惑最大的借鉴。
以我的并不优秀的智力,我听了以后还是能够感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我说的悖论金雁先生一定不要认为我是在批评她的,其实我认为演讲者呈现出一个悖论,既是问题本身的巨大深奥,也是研究者能呈现出它的微妙。这个悖论就是,毫无疑问,无论是你说,还是我们听,都看到了第三派人实践的巨大魅力,可是你呈现的第三派在当时是失败了,在历史上是消亡了,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种历史可能性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能够死灰复燃吗?它曾经就是死了,它曾经在实践当中打不过另外两种势力的,前有沙皇政府,后有布尔什维克,它是失败的,是死掉的。这样一种尴尬其实在今天也一再发生着。比如说六四广场上,一边是即将可能要进行镇压的政府,一边是坚持绝食的学生,那时候有没有第三派?有,说我们要撤。自己给自己搭台阶,我们已经胜利了,撤。有人听吗?绝对不会听的。
六四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在美国的一个不同政见者,这应该是一个最老的洞见者,比陈明、王君涛资格老,他的言论也比后来我们最优秀的吴萍的言论还要早,这是当年大字报的执笔者,后来因为与李正天分道扬镳了。他说,我有必要说说,李正天这个轰动中国的大字报,我是执笔人,不是李正天。王希哲现在在美国,他的言论我们能看到只言片语。他是两度进监狱的一个右派,到了美国,现在是左翼。当然我也很惊讶,王希哲说的,只有左翼才有魅力。不同政见者,你们懂得吗?我是一个地道的右派出身,“只有左翼才能赢得民众”。左翼思潮毫无疑问是有巨大魅力的,就像这个东西最后为什么它就溃败了?也是说明左翼思潮是因素,中庸太好,但是中庸在人心上吸引不过人家,所以你败了。毫无疑问,这个东西对我有巨大的感召力,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历史中,在现实中,它未必是胜者。所以现在演讲者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凭什么要鼓吹它?它是失败者。还可以这样说,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有魅力有什么用呢?你有魅力就是把苏联引向灾难。你的言论倒是有魅力,一点不假,列宁、托洛茨基的言论太有魅力了,但是你把俄国引向的是灾难。好吧,我知其不可而为之,支点就在这儿呢。
我认为改造社会毫无疑问是两个出路,一个是社会太糟糕了,打碎了重建;还有一个就是顽强地在旧肌体中生存,发展新的因素。虽然我前面说了,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点上,激进的反对派非常容易占上峰,但是这一激进思潮不是分别把俄国、中国引向灾难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旧肌体中慢慢地生长。我是这样想的,我把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作旧社会来看待,就像共产党把国民党的社会叫做旧社会一样,我憧憬一个新的社会。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肯定都不满意了,如果新社会来了,我们就说这是旧社会。
我觉得新社会的生长点在哪里呢?所谓生长点是有可能性的,不能太无可能性的。一个是民间宗教。原来我有点失望,我认为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代表的民族太唯物主义了,不可能信奉宗教的。但前两三年听了一个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演讲,讲儒学在台湾之类的内容,其中讲到台湾民间宗教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是那一小部分是让我极为震惊的。因为我前所未闻,就是台湾解开党禁以后,民间宗教发展得这样迅猛,在吸引民心、在吸引民众方面,大批的人加入各个派别的民间宗教。因为民间宗教帮助人们的心灵,所以人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些宗教拿到大笔的钱要办学轻而易举,动辄上亿资金,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个。这就让我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原来我不相信,包括我自己也是僧道无缘,从来不烧一柱香,从来不拜一处佛。虽然有时会被大和尚问到你一柱香不烧来干什么?原来我不相信中华民族能皈依宗教,但是看到台湾的事情不得不让我重新认识中华民族。我们如果真的打开了以后也是有可能的,而这毫无疑问是新社会的一个生长点。
还有一个是医疗健身。这是一个要紧的事,靠医院是荒诞的事,我们的健康怎么给它了?在它那里呆了一些天,出来就好了。健康毫无疑问主要是要依靠自己,而我们中国的传统宗教一大特征就是把医治心灵和医治身体合为一体。所以法轮功这个事儿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因为法轮功太粗糙了,但凡有知识的人都会对它嗤之以鼻,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应该是一个极大悲剧,因为不允许民间宗教的尝试。如果允许尝试、允许竞争,粗糙的肯定要被精致的所取代,那是一定的。但是精致的还没有出来,灭绝粗糙的了,而且同时宣布不许民间宗教大肆活动,这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再有一个是民办教育。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点。
我讲的这些,像民间宗教、民间健身、民办教育等等,就是我说的那种,我们新的生产点应该有一批人,叫知识人也好,叫非学院派的人也好,就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些人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性质呢?第一,这些事情不是做学问,也不是在搞思想,是做事,也不是做商业,并且也不是在做狭义的慈善。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有别于政府的,让社会较好地运转所必需的一些事情。他们在政府之外,做民间宗教、医疗、教育。这样的活动我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萌芽,比如说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陈嘉庚办教育。
最近我到汕头大学去过一次,我觉得那个气象很让人震惊。有意思,这里到处都是洋人。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学校的资金来源,这完全是一个国办大学,但是他们的资金来源有百分之四十几还是五十几是李嘉诚基金会掏的钱。李嘉诚基金会认为,我掏钱了就不能不参与学校的管理,所以李嘉诚基金会就派了两个文化人在这儿做监督,我要监督钱怎么花,我要参与学校的管理。有了钱了,它就有力量,学校很在乎这个钱,有那么一大笔钱来帮助我们。人家的钱给了,也不是让你打水漂的,所以我要监督,所以那个学校办出了一些很新的气象。首先,图书馆太有意思了,同学们都包在书中。全部都开架的,而且开架不是说存书的地方,而是读书的地方和书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形式。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的外教数量,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比例就更不要说了,在中国大学里可能首屈一指。还有就是院系主任由外国人做,在中国的学校里是首屈一指。这都是李嘉诚这个大财东要干预、影响中国的学校,也就是说李嘉诚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当然30年代很多人办教育了。到21世纪李嘉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深刻地影响。
我也去过四川一所学校,他是一个大商人,与李嘉诚比不了。他是借鬼怀胎,在重庆邮电大学出钱办了一个学院,因为那个学院起步的时候必须是三本,招的学生就太差了。但是就办起来了,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校舍、教室一切都是他来指挥运转。这简直是国中之国啊,我们不准民办教育嘛,他借鬼怀胎,真就办起来了。
所以这些事情还是很有努力的余地,就是社会上要有一些人,这些人的理想不在于赚钱,不在于钻进政府的系统做一个公务员往上爬,这些人是以今天中华民族高度世俗观的,这些人肯定是非常异类了。这些人就是要帮助民间社会发育,就是有这样目标的一些怪物。我的悲观就在于中华民族这些的怪物大概太少了,我们现在都是如此功利,都是功利化的教育导致的。这些怪物太少了,这应该是一件是令人绝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些怪物,真的这些怪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以有人先做商业,然后转过头来用大笔的钱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我不是要沽名钓誉,是要深刻地影响你,要改造你的教育。我居心叵测,绝对要改变你的教育。真的要产生这样一些怪物。
再往宏观方面说,要在旧肌体中生长,其实不外两大出路,一个是走费边社的道路,不革命走费边社的道路,走费边社道路就是说我们永远不在政府当中,但是我们要与政府的首脑对话,我们要说服他们,我们坚信我们知道一些好的道理,对大家都有利,能造成双赢。政府的脑筋很好使,它为什么不能听呢?费边社的道路。
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最像费边社的组织,但是政府不买账的。明明是这么不激进,这么像费边社的智者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没走通。没走通不要紧,接着尝试,又换届了,对不对?还可以接着尝试,不屈不挠地,是不是?这个政府前任的时候肯定是走不了。走不了的话,可以从两个人身上看得最清楚,一个是从茅先生,一个是从李洪志。这两个人都是应该进入政协常委的。如果早把他收编了,李洪志何至于最后走到这样一个悲剧?茅先生没有到人大常委,没到政协常委,这就是政府不大允许你们这些智者在体制外好好帮忙。
第二条道路就是埋头做自己,让社会肌体重新发育,朝新社会发育的一些事情,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这样的人有坚定的理想,但是看的全是小事情。他们就不以为大事情能影响中国,他们就以为那大事情就不对,大事情不是我要操心的事情。每个人、每个组织其实如果有自知的话,都应该认为我影响不了天下,我只能影响一个学校,那就算很不错了。我只能影响我的一些教徒、信徒,那就很不错了。加在一起,才有中国的变化。方法论上,他们应该笃信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尽管他们有非常坚定的理想,但他们不屑于做那些太大而化之的事情,因为在方法论上他们就拒持那样的思考方式。那样的思考方式是革命党,是很多乌托邦制造的。乌托邦制造者也很伟大,是乌托邦制造者的方法论。他们这样的人是坚定地持有另一种方法论,只有积少成多才能导致变化。他们不相信一个外科手术来了以后会怎么怎么样,他们做的事情反馈回来肯定没有大成果,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小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方法论,所以他不会因这样的小反馈而失落。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张曙光:好,下面我们请翟志勇博士来评论。
翟志勇:谢谢张老师,谢谢金老师。
事实上,我就属于金雁老师所讲的对第三种人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在俄国—苏联传统中有这样一段历史,有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看了金雁老师的文章,听了她的报告,不仅弥补了历史知识上的缺失,也深感金雁老师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有很多争论,而在争论的背后,也有诸多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NGO及其他的基层社会活动中,如于建荣教授发起的“随手”公益活动,这与当时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活动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雁老师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建中国社会,确实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阅读金雁老师的文章时,我有几个疑问和困惑,想借此机会请教一下金雁老师。第一,对于地方自治局或者地方自治运动,您讲他们在农村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不知他们在城市里面是否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第二,他们除了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说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之外,对于整个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这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有关联,就是说他们最终可以战胜沙皇,成功地从沙皇的官僚机构中夺权,取代了沙皇政府,那么为什么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在苏维埃政权还很弱小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战胜苏维埃,反而被苏维埃最终战胜?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因为有个总的困惑,第三种知识分子开创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最终的失败,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是不是第三种知识分子或者第三条道路最初的思想或设计中存在某种缺陷,使得他们最终没有办法来应对苏维埃?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依照您的研究,您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运动或者社会组织中是不是同样缺少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有可能会使得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努力将来也有可能会付之东流?我想这种可能性还是会存在,今天虽然很多社会组织做了大量社会重建的工作,但是依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可以预见,他们一定会成功。
张曙光:好,我们下面请盛洪来评论。
盛洪:非常感谢金雁教授,确实很短时间告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在逻辑上是接受的,因为我最近也在反省过去对历史的理解。因为我们脑子里的历史实际上是被灌输进来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关于历史的非常简化的按照一套即定的理论模式来描述的,而这个描述非常简略,用几句话概括,甚至一个大学生在高考的时候背下来就以为他理解了历史。但是我觉得那是错的,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小历史,我认为那与大历史完全不一样,而且那些被讴歌的一些大历史其实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在东方世界,在近代以来有关革命的事件几乎都是值得批判的。因为在我看来,革命这个词在中文来看,实际上就是汤武革命。汤武革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有限定使用的一个词。儒家是肯定汤武的,但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才同意使用的暴力,甚至在儒家内部还是有很多人反对汤武革命。比如像王阳明,他讲过,倘若周文王在的时候,他也不会动武;孔子也说过,武王伐纣,“未能尽善”,就是还是有很多批评的。所以虽然一个社会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理由,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非常谨慎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近代以来存在一种对革命的讴歌,无论是左、中、右知识分子很难有人抵御。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就是说,您刚才讲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我基本是赞同的,就是看小历史。历史是每个人体现的,不是一两个伟大人物一挥手,历史就发生剧变了,这没有意义。实际上历史是每个人亲自体验的,他高兴,他幸福,这才叫历史,不是有个伟人发明了一句话,然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剧变,制度发生了什么改变,不是这样的。我真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这几乎就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可以说中国革命、俄国革命,还有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因为我看了印第安人的悲惨结局,其实是美国革命以后,其实是为这些在美洲的殖民者向印第安人扩张,去掠夺他们的土地、屠杀他们铺平了道路。而在这之前,英王对印第安人还是相对仁慈。所以这一点不能很简单地去听美国人主流的那种宏大叙事。
我觉得需要纠正的可能有好多。简单地说就是,第一,所谓的历史进步论和五阶段论,那是一派胡言,说实话根本不存在那样的历史。比如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我最近有个体会,稍微讲点小事。一个是我最近研究土地问题,然后我就研究英国的土地史,我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英国的土地一直是封建制,真正的封建制,就是那种英王、领主、封臣和保有人的制度。这个制度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大概在1925年,就是在法律上真正结束是在1925年,一直是这个制度。那么,大家会问一个问题,怎么会在这个制度下,在全世界率先出现工业革命?我说,这个问题恰恰在于你相信了那种五阶段论,其实这种土地制度与工业革命根本没有矛盾,或者说在这种制度下,它有各种变通形式,能够让它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存在问题。你再反观中国的土改,中国土改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它可以用暴力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且在消灭他之前,还要虐待他。我们看了大量的记录,当然可以看看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看很多真实的记录。他们(共产党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因为中国当时的土地制度是最落后的生产方式,他们对资本家还可以宽容一点,“我们不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消灭的话,中国就没法现代化了。”我觉得这个理由不能成立,这是很荒诞的事情。而且严格来讲,我们去看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秦汉以后,中国的土地制度就不是封建制度,这是最重要的,它就是交租、纳田赋,这个制度与英国是没法比的,几乎就是现代的契约制度,而且在契约之下还有永佃制等等。这些东西简直就是很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要用暴力去把它推翻。这是很荒诞的,我看死了几百万人,所谓地主,把他们杀了,杀之前还虐待他们。这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罪。
还有一个故事我想讲讲。我前一些日子到广东,去广东省博物馆看看。我发现一个问题,其实广东在近代以来,民间就在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很多的广东人很早就与海外联络和交通,甚至有些做工人被卖到海外、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带回来大量的海外的文化、技术。作为一个港口,广东和广州这个地方的产业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在有效互动,广东省就出现很多产业,都是为出口而形成的。不仅是有西洋画的陶瓷产品,丝绸和茶叶等,还有银器、绘画、壁纸、广彩和绢扇等等,全是针对出口的产品。大家再看看广东的碉楼,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很自发的一个现象;那些从海外归来的人会把外国的文化资源也带回来。所以我们可以坚信一点,就是那些人的谎言,就是“我们不通过暴力没法实现现代化”,是一派胡言。其实这种自发的市场制度会使这个社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地、不断地改进,根本不需要通过暴力。
反过来讲,刚才讲知识分子,如果说第三种知识分子有需要批评的地方,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好,只是一点,他们是失败了。这个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暴力,没有掌握政权,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文化传统的主流。我觉得这是核心,其实后来所有这些人,包括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可能在当时,在不同思想的交锋中占了上风。第三种知识分子既然信奉自己的主张,但是没有在俄国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占主导。而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由某种思想来指导他,他杀人是认为杀人有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所以现在的任务,我们简单地说,有体制派和反体制派。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是批判体制的,但是我们并不批判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人其实只是体制内的演员而已,核心是体制的规则,而批判的核心恰恰是反对暴力,反对强制性的,强调的就是自发的秩序,强调的是和平的演进,强调的是对暴力的约束。如果多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不仅是给农民看病,不仅是给农民拖拉机,我们日复一日地去强调这一点,就会有效果。而且我认为这样一个多世纪的暴力革命,到头来一看,其实白死了几千万人,还要从头来。这个事实已经给了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思想一种强有力的支持。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认为应该更强化这样一种主张,不断反复去强调而使得这样一种主张去占上风,有可能去影响未来的知识分子、未来的政治家,可能会改变社会的走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做的。
我就评论这些,谢谢!
张曙光:好,谢谢,下面请赵农评论。
赵农:谢谢!金老师今天讲的这段俄国历史的确非常稀缺,其他人很少知道这些。听完之后容易产生联想,即想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是不是也与它有类似之处?既包括知识分子的一些情结,也包括那时候“少谈点主义,多思考点问题”,这是胡适的主张。然而,如果把他的话撇开,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真正有主义的人。这个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只不过当时信奉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而已。由此引申出来的话题就是苏维埃产生暴力革命,旧制度下革命需要不需要暴力,是不是能够通过一种不流血的、小事积累的方式,最后来完全改变这个社会?我感觉也不应该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因为时代都在发生变化。
我举一个例子,是否当时俄国在二月革命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对于现代文明的元素,对于普适价值的理性认识有现在这样强吗?我认为要比现在差许多。中国曾经在清王朝覆灭之后,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还没有完全强势之前,有一段地方自治的时期。那么我要问,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包括阎锡山、李宗仁等等,中国地方割据里面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类型,照样还是原来那种,原来是督军的,一上来还是由他说了算。还是通过政权力量来多征点税收,以政权力量来办教育、来开矿山,阎锡山不就是这样干的吗?这就让人感到非常有意思,就是即使给了自治的机会,但结果仍然是,一群土皇帝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以为,革命就是底层这些人或者是受到了某个领袖的煽忽,或者是受到了谁谁谁的蛊惑,但从来就没有把责任放在那个专制者头上。究竟是谁让他们变得那么激进?你能允许不同的人说话吗?你能允许知识分子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逐渐地改造社会吗?天则所是一个很温和的、主张很理性的,不也动不动就要关你的网站,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这个责任的定位要更加明确。
第三点,我认为,基于专制条件下暴力革命所付出的代价的强烈恐惧,我们仍然理想化地去寻求一种好像不通过流血也能改变社会的途径。我认为这多少有知识分子软弱的一面,甚至是在缷责。因为他知道在那些专制条件之下,真正要做什么,代价是非常沉重的。这个代价不是你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强加给你的。谁都不希望流血。如果你要结社的话,那你就要被抓起来,你的肉体也可能被消灭。也许我的看法稍微有点另类,但我把这些问题都摆出来,以供大家思考。
好,谢谢大家!
张曙光:好,这样,我来讲一下,然后再请你来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
听了你讲以后,我有一个问题,民粹派是不是就等于第三种人?
金雁:不是。
张曙光:对,因为这个概念你在里面讲的,我现在好像有点清楚了。因为民粹派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一个贬义的。
金雁:这个词在当时的俄国是一个褒义的。
张曙光:再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现在从历史上来看,第三条道路没有成功的,有历史的先例没有?我看没有。
郑也夫:人性有很大的弱点。你说的那种很扎实的、慢慢渐进的道路,在好多时空之下,民众不买账,要听大的忽悠。我们保守地说,这也叫悖论。
张曙光:我们想一个问题,要结束这个专制的制度,恐怕不是第三种人,当然这个基础他们会铺路,这个是,但是真正在那一点上,不是他们的,而是专制者的,有权力的人。这也可能是一个悖论。
我们想一想,刚才你讲到台湾的社会状况。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不是一下完成的,蒋经国说我是个独裁者,也是最后一个独裁者。这是蒋经国自己讲的。当然你说蒋经国的思想是不是独裁,这可以另外说的,恐怕真正变革的状况还是要把各方面情况结合起来,单独的一条第三条道路,我觉得历史上没有成功的。你想想,哪一个大的变革是第三条道路成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解放前,国民党一个、共产党一个,民主党派实际上是标榜第三条道路的,不是靠到国民党就是靠到共产党。和国民党闹翻了,最后靠到共产党。靠到共产党,最后变成现在这样子,几乎没了,对不对?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
甘地也没有,曼德拉最后是谁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是非常有意思的。
郑也夫:张老师就是说开明统治者也造就了历史,蒋经国肯定创造了历史。
张曙光:肯定的,是这样。就是说,打破这一点的,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说第三条道路也许积累了、奠定了很多东西,但是为什么俄国的第三条道路最后走向了那样,而台湾或者其他的地区可能能成功?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答,需要我们去研究,就是要研究一下,第三条道路为什么失败?它要成功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成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我觉得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解释不清,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还做得不够。第三条道路最根本的局限性在哪里?医疗、教育等等都需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最后要把这一套理念推进去,要没有那一个东西,我看很难。因为你专注的那些事情,必然忽视另一些,这是人性的局限。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的脑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全身心投入这个的时候,你对另一个就忽视了,而另一个东西可能是决定你命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恐怕这个问题深刻的地方可能远不是我们自己现在想得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金雁今天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除了讲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去读书,去总结人类的历史来得到一些进一步的认识。
我就讲这样一点,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请你把大家提的问题做个回应。
金雁:张老师说的第三条道路其实和第三种知识分子有不太重合的地方。因为我刚才讲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之所以要跳出革命和体制内的选择,他没有宏大的设计,不是宏大叙事,他们只想有一个很简单的人民少流血,知识分子可能作用是什么。
刚才有人问他们生活来源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多人想知道。大家首先要知道俄国知识分子的起源是什么?俄国知识分子是从贵族起源的。贵族是什么呢?贵族是当兵的。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只要你参军打仗,立了功,就能得到土地,你就成为贵族。但是有了土地没有用的,俄国的土地非常广阔,俄国就需要土地上的劳动力。俄国银行贷款通常不贷给没有劳动力的土地。这样,他们就争夺不过像教会这样经济实力强的,因为大家都在争夺劳动力。俄国最缺乏的就是劳动力,它就要国家用立法的形式以保证土地上的劳动力不能流失。这样就是俄国的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与西方的农奴制不一样,他不是契约式的,是国家划拨式的。这就决定了俄国的农奴同时也是国家的纳税人。
关于这一点,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秦晖就问过我,为什么俄国农奴会纳税呢?我当时就对他说,那就是双重剥削吧,国家也剥削,农奴主也剥削。这个问题其实我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佃户只交租不纳税,欧洲的农奴,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佃客、部曲这些人为什么与国家不发生关系?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发现,俄国就是国家划拨式的,他第一身份是国家纳税人,第二身份才是用劳动力为贵族补偿征战的代价。所以在俄国,贵族是第一等级,僧侣是第二等级,与西欧不一样。这就像石拱桥一样,一块石头压着一块石头。可是俄国部队的征战力实在是不行,后来有了哥萨克,有了雇佣军,它就不用贵族了。因为俄国不断地扩张,它有能力来收买贵族阶层。
1762年有一个《贵族解放法令》,这也是我非常纳闷的,什么叫《贵族解放法令》?我曾经讲的时候,有同学在下面嘀咕“贵族解放还叫贵族吗?中国怎么没有地主解放法令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俄国的贵族其实就是军事农奴,是国家的第一等级,但是他们也是极端的不自由。但是因为征战,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都是国外的应用教育,全部都是法人教育。1762年贵族解放了,那么农奴解放不解放?这就不对等,所以很多人就呼吁农奴解放,农奴解放成了一个政治运动。沙皇为了置换经济权利,你们贵族不要要求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一搁就搁了99年,到1861年才农奴解放。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贵族都是领地的,我找工作只是玩票,那么俄国就会产生多余的人,也会产生一大堆的文学群星灿烂。他们有时间,俄国的作品也会出现那种,现在年轻人读不下去。那天王炎说,一个白桦树写18页,因为他们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俄国这种寒冷高纬度的地区,他们只种一季庄稼,漫漫的250天的冬季,男人不酗酒是活不下去的。
这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很多人在生活上,像果戈理、库格涅夫等等,很多人都做过国家的公务员。最后俄国有一个罪叫流放领地罪,你捣乱了,流放到领地,你不能到城市来。流放领地算什么罪行呢?只不过是你自己不能到城市来,但是其实你是衣食无忧的。这样就有很多有良心的贵族,他们也知道剥削农奴是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了大量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又离不开农奴,所以他们就要忏悔,他们就要面对农奴做事,这就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起源。
所以刚才有人说,我们没有办法,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当然到了后来,地方自治局有募捐,也有基金会。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地方自治局有财产资格,但是也有国家划拨。因为当时国家下放权力,国家也划拨,而且也允许它征税。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来不及展开。时间有限,我只能宜粗不宜细,其实大家刚才提的很多问题我在那本书都有考虑。因为我是用不惑之解来给自己解惑的。我解惑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小的问题都搞明白,你说明了这一层,没说明那一层,那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大家都看完书,可能就会觉得原来很多问题我已经解答了。包括大家说的,为什么他们不去搞启蒙?因为搞启蒙的大部分是革命者,搞启蒙碰壁了。为什么他们不搞立法?搞了很多地方立法,他们的地方立法才促使了1905年沙皇的立宪君主制。这些他们都做了。大家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觉得刚才也夫讲的有一半对,一半不对。一半对,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左派是有魅力的。左派的动员能力、许诺能力等等,都是有魅力的。但是如果在专制下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什么左、右派之分,而且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左、右派概念本身就与欧洲是错位的。之所以沙皇没有灭了他,而布尔什维克灭了他,就是说他们面对一个更大的政治的时候。他们的发展当然与战争有关系,如果不是一战,他们不会一下做得那么大。因为战争状态下,沙皇本身的腐败无能,逐渐地退出很多领域,给他们钻了空子。
他们被灭掉还不是因为他们制度设计不够。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当时布尔什维克这么小小的力量在内战中能够打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们那么多人打着旗帜——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不是归苏维埃,一切力量都团结在立宪会议之下,你们为什么打不赢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第一,我组织的军队采取的是人治法,三万全都是沙皇的军官,你们的家属我全部都控制起来。你们敢去倒戈的话,我杀你们全家,诛连九族,你们敢去倒戈吗?第二,只要你往后退,军事法庭采用的完全是XX法。而且口粮的供应也都是这样,你不上前线你就没有口粮。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对面是一盘散沙,有立宪的,有保皇的,有与国外勾结的。他们自己之间就打得一塌糊涂。
布尔什维克有一句话,我觉得列宁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任何情况下,我的对手只有一个。在我收拾这个对手的时候,对所有的人我都可以原谅,都可以暂时放下来。双十革命的时候,有人早早就看到了,说列宁先生,如果您胜利了肯定第一个就拿布尔什维克开刀。他说我等到把社会革命党杀尽的时候,我第一个会杀的就是孟什维克。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联合社会革命党,然后又要先杀社会革命党?他因为社会革命党是恐怖主义,他要先联合恐怖主义把所有的对手干掉的时候,然后我就害怕你用恐怖主义来干掉我,先把你干掉。在这一点上,他绝对的手段高明。所以很多人说,他的存活,如果沙皇政权或者临时政府的政权延续的话,他肯定不会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我这里因为为了矫枉过正,过多地强调了他正面的地方,他其实负面的地方有很多,我都没有谈到,所以为什么我说对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批评都有。现在在列宁前面输上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你会看到,所有的评价都是反面的,只有那么一两句话觉得还可以,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的确,他有很多方面可以值得我们来讨论,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方面,而是他没有面对一个更强硬的、更专制的政党和政权。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当时沙皇退位的时候,让他的弟弟来继位。他的弟弟说,如果立宪会议授权,我就摄政。我儿子来继位的话,我摄政。但是如果立宪会议不授权的话,那我就退让。列宁说什么?列宁当时在那一天——1918年1月5日,在这之前,他就说立宪会议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政权,工人上街游行的时候,赤卫队开枪枪杀,现在我们在档案中看到最少有21个人被枪杀。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禁止工会了,独立工会还敢上街吗?然后采取了所有的政党都想到的,我们要做到让列宁没有话说,我们就要做得比他更社会主义。列宁采取的是什么方式?会场是开放的,所有的伤兵都可以进来,每个人的发言都被一片嘘声嘘下去,连列宁的手枪那一天都被别人顺走了,可想会场的秩序乱成了什么样。文人在那儿坐而论道是没有办法的,最后开到四点钟的时候还在开,就宣布先体会,明天再来。结果第二天就封上了,立宪会议就已经封上了。然后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人民没有批准这样的选举。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牵强,你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24%的选民都投了你的票,你现在说人民授权作废了这个选举,这些东西都是假人民之名。
在内战的时候,实际上是孟什维克来帮他打内战。孟什维克说,我们这个时候放下前嫌,他毕竟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我们只要帮他,将来在这个平台上肯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结果打下天下,第一拿他开刀的,就是社会主义者。非常有意思,有一份刊物,他们办的时候叫《白天》,然后布尔什维克就六次取缔。第一次取缔,他们就叫《傍晚》;再取缔,他们就叫《深夜》;再取缔,他们就叫《深夜》;再取缔他们就叫《茫茫深夜》;再取缔,他们叫《不见天》;最后他们这个刊物只能到国外去办,叫《未来》。这就可见,社会主义的希望在面对这种专制的情况下,就只能在国外,在未来来体现你的这种诉求。
也有人说,为什么这些理想主义者会发生这种蜕变呢?这个问答必须要回到我那本书的第八章,谈平民知识分子,就是平民知识分子从一开始针对贵族的时候,他们本身就有很多特质。第一,他们本身就是波拿巴主义者,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赫尔金说的。他们本身就有很强的愿望,总愿意规划别人,他们觉得芸芸众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生活,只有这些精英阶层告诉他们,我带领你们走出黑暗。在这种状态下,有太强的强制色彩。
再有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导入的话,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平民知识分子,他那个时候在沙皇的状态下,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来反对恶,那么我就是恶来反对恶。他创造了一个理论,就是如果通过善不能达到的,那么我只能说目标是正确的,手段是忽略不计的。我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善,这就没有办法。我哪怕用恶来达到善,将来的善应该说也是正确的。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来说,他自己被沙皇流放了17年,应该说理论的实践他没有看到过,但是他这个东西给整个革命民主主义,包括布尔什维克导入了一个传统文化,就是手段忽略不计。在俄国的革命者里面大家都是这样,心照不宣的。我要搞钱嘛,种鸦片、印美钞、抢银行,利用警察局来解决对手,所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善良的被淘汰者。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法考量的,所以理想主义者最后都会发生蜕变。到最后,大家就会觉得我们的理想与这个设计完全都不一样。斯大林就说了,“如果按马克思说的话,我们早就关张了事了。你现在是要关张了事呢?还是要继续我们的政权呢?”没有人吭气,大家都默认了关张了事。而且斯大林也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脱节的地方,他与那些哲学所的人说,养着你们这些人就是要你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弥缝工作,他非常明白。
我们一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给我们送来的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已经完全民粹主义化了,甚至超民粹主义化了。我这本书里面把这些方面都有谈到,就是列宁怎样发生这样转变,他的思想中怎样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些东西。所以后来的辩证法,他的一些东西,拿到政权是首位的,其他的,我全都忽略不计。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路径依赖后来就使得俄国共产党里面出现了多少丑恶的东西?这也是他能够实践,也是他能够发生蜕变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盛洪:我稍微插一句,这些人其实是理想蜕变呢?还是一开始就是为了夺取控制权,而借助于这种所谓的……
金雁:很多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列宁对各种理论都非常娴熟。当时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他已经移居美国了,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看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当时有一个人就是帕乌斯基告诉列宁说,因为这是一个俄裔的德国人,然后社会革命党人在做军火生意。他说,你用德国人的钱,你用不用?恐怕不能用。他就告诉他,既然你所列的理论设定和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用?
列宁经过一个通盘考虑的以后,觉得还可以,既然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民粹的这一套理论已经奠定了,所以现在有媒体说了,是8500万欧元。
盛洪:就是满腔的热情没有实现?所谓的理想,还是说为了争取政权?
金雁:他当时有一个讲话,他说我们在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来利用资产阶级的钱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有什么不可以?
盛洪:我想说的是,他这种话是辩护性的话,还是一种真心表达的话?就是我们弄不清,他是真心为了那个理想,还是在说那个理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欺骗别人?
金雁: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不是列宁肚子里的蛔虫,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但是我可以说,他本身的理念,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利用的成分。他与托洛茨基商量过,他说如果内战的尘埃落定以后,我们的阀门是需要松一松的。我们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平台,可以有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他讲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后来就发现,如果面临其他派别挑战的时候,我的根基依然不行,然后逐渐地先打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清除的时候,所有的社会主义说,反正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是自由主义。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下一个链条就会轮到他们身上。所以后来列宁是一步一步地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在摇摆,一直到他大权被架空的时候,他说了很多——我们对不起工人阶级,我们的理念蜕变等等,他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列宁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曾经多次跳跃,以及我在70年代把《列宁全集》作为教科书来读的时候,我就总是跟不上他。后来有了电脑以后,输入一个关键词以后,你就发现,此列宁打彼列宁。普列汉诺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反对新列宁,不是因为我反对他个人,而是因为新列宁打倒了旧列宁,他赞成自己过去反对的东西,反对自己过去赞成的东西。而列宁这种跳跃我后来屡试不爽的都可以战胜别人的手法就是,很多人讲出来,你怎么这么反对的语言?我说列宁全集你去查去,多少卷多少卷,因为他相反的话讲得太多了。我可以判断大概在什么年代,他的思想处在那个年代的话,他肯定会讲什么样的话。
我们当时有一位郑一凡老师,一直就是列宁的铁杆粉丝。后来我就一直不明白,后来看到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时候,恰好他被架空的时候,那时他的政治遗嘱对所有大的官僚化已经发出了置疑的时候。但现在如果翻07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列宁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我在中央编译局翻译列宁全局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站在这个年代的人和站在那个年代的人,两个列宁在打架。所以后来剧变以后,人们就想起了三个列宁、五个列宁、八个列宁。那就是因为他每个阶段都在变。我敢说,如果列宁再活多少年,我敢说他还是会变。现在很多人说的一句话,新经济政策多好啊。如果按这样走下去,苏联哪会剧变啊?但是那只是他一时一事。所以刚才盛洪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这一点?列宁是一个策略至上者,他的理论非常娴熟,他总是把民主和专政拿在手里。他认为我自信的时候我就搞民主,不自信的时候就搞专政。可是他这种自信力是没有道理。后来他24年就去年,去世得又早。但是这个阶段你说他有没有对自己怀疑的地方?的确,列宁是一个可以检讨自己,把自己以前都推翻的人。这就使人们很难猜测,他的确是想用这个东西,还是他有这样的考虑,但我可以这样说,他越到后来政权拿到手的时候,他距离的理想状态就会越来越远。因为指问他的人大多了,这么多社会主义者都在问,你当初的理想呢?你所说的与你所做的、与旧沙皇有什么区别?那时候沙皇对政治犯远远要比现在好得多。
现代档案出来以后,我们就觉得,第一,张老师说的,历史原来是这样,历史根本就是被编造出来的。第二,这个细节一点点垒起来,你才会发现,其实比我们这种简单化、模式化和公式化的东西,远远要复杂得多,因为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这个世界的变化也是这样,此起彼伏。所以你不能把他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好人,一个恶人,他是此一时彼一时。但是他有一个环节,我拿到政权,没有它,绝对不可能有十月武装起义;没有它,也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个时候就是清一色的政府,对克伦斯基政府已经通过了不信任案,你不武装夺权,我们也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府,只不过就是合法授权,可能会出现魏玛状态、魏玛共和状态,后来又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我们肯定绝不是后来所导入的这个轨道。这个轨道与列宁本人的意志有非常大的关系。
1921年传到中国的当然是列宁主义,是共产国际后来这种不择手段的列宁主义更多一些。因为当时毛泽东比较喜欢这个东西,毛泽东法家传统非常浓厚的一个人,他觉得非常合拍。因为整个俄国的传统,比如贫民知识分子,一直在贵族那边,就是那边特别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们在大学相遇的时候,那些富二代都是说法语,都是谈哲学的。而另一些僧侣阶层出来的人,俄国民间僧侣有22%的革命骨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当时也觉得,这像米罗诺夫,办一个社区大学,大家都在问这个米罗诺夫之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就是因为俄国历史上东正教出现过,他有很强大的民间宗教,然后官方把这个民间宗教打压下去了,有十分之一的人信仰民间宗教。这些人就四处逃散了,不交税,没有身份证,不去征兵,不去边境省,这对俄国思想的影响非常大。这样就使得俄国的宗教界非常保守,因为他政审非常严,他怕那些不同宗教的人混进来。这样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职业少,他控制了教育资源控制不了就业资源,所有的人都是无法就业的愤青,大概有十万的职位,但都是自然地退出。如果没有自然退出的话,你就递补不上去。但是有多少人呢?有几百万人,大量的文化程度高,而且他又是本国文化受教育,所有的贵族受的是外国教育。所以了解本国的都是这些僧侣阶层,他们最后成为激进主义,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个渠道。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三个人都是从僧侣家庭出来的,他们先搞文艺评论,所以我说文艺评论本身就是一个激进主义的摇篮。
他们与托尔斯泰有几次非常激烈的冲突,托尔斯泰就说,你们写不了小说才去搞文艺评价。如果你有本事,你也写小说啊,全部都是很左的这些人。他们导入的这些思潮逐渐地传承下来,到了革命者手里,到了列宁。因为列宁是律师家庭出身,也是属于这种贫民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在大学里面对那种富二代特别反哲学。因为富二代最爱谈哲学,黑格尔是他们挂在嘴上的一个名字,特别爱讲外语,这样搞得一些平民知识分子在这些行为方式上,那些人都是沙龙里长大的,因为沙龙是只有贵妇人出入的。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派的精神导师,才有了后来的到民间去的活动。民粹派很长时间在俄国都是一个正面的,只是到了现代以后,我们才把它变成一个负面的。因为民粹派这个词,就是人民的集合,但是它有几点,我们需要稍微把民粹派做一下辨析。一句话,就是因为俄国的村舍传统,俄国的这种重集体主义,民粹派是非常反对自由主义的这种个人、个性的,这与俄国的生存条件有关。我一说这个,秦晖老师就说我是文化决定论,不是文化决定论,但是要考虑到地理条件。俄国的地理条件的确存在着文化生存的背景,是不能够割断的。
我就说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张曙光:今天金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我们对俄国的革命可能需要重新来认识,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来思考和研究,确实现在的问题太多了。我想谢谢金雁老师,谢谢今天的几位评议人,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