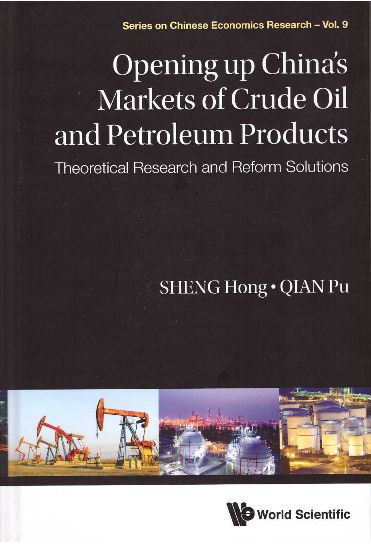赵农:
谢谢张老师真诚的批评和建议。
茅于轼:
我耳朵聋了,大部分听不见。我说一点感想,农民的上访,农民在中国是最没有特权的一个群体,他们上访是有一种权利意识或者是利益诉求。从权利意识来讲,他的权势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里面最没有特权的,所以他的权利诉求是一种最基本的权利的诉求。他不像除了农民以外,特别是我们的政府,他有很多特权,他们的权利诉求就很值得怀疑。所以我说农民的权利诉求是基本的权利,哪些是基本权利?他自己感觉我有理,我是正当的,所以只是一个基本权利的认定问题。再一个,他的利益诉求,他认为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什么是正当的利益?就是他不会损害别人。我们有很多特权阶层,他有很多利益诉求,他是损害别人利益的,而且农民还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权利的最低层,还有一个就是他比较朴实,他不会拐弯把黑的说成白的,我们有很多学者有这个本事。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报》登一篇文章叫做“毛泽东不是独裁者”,这个是金仁(音)写的。我就很惊讶,学者就是有这个本事,他说毛泽东不是独裁者,全世界都认为他是独裁者,他居然认为不是独裁者,农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只有一部分学者可以写这样的文章。
所以农民的诉求,利益的诉求,他是很正当的。什么叫正当的利益呢?我觉得就是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他受到了侵犯,所以他有这个诉求。所以讲权利也好,利益也好,最根本的正当性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人权。所以,我觉得对于人权的认识特别重要,我们国家已经把人权写在宪法里面了,但是在很多场合你要谈人权好象还有点风险。法律上、宪法上规定人权,但是在实际上人权很难得到保障。
张曙光:
我再说一句,刚才有一件事情没有说。就是他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访的人好多被边缘化了,在农村社会里面,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上访的,尤其是贿选的这些人,甚至在农村社会里面有流氓心态的人。他这个上访就和你的解释不完全是普通农民正当的一些诉求了,也可能是有另外一些东西。所以,他和你刚才讲这个实用道义意识的也好,他是另一面来证明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讲你这个道理,你得把你那些材料充分展现出来,因为你只讲了他们边缘化这个事情,我就想既然是一种正当的诉求,应该说得到普遍的支持,怎么又能被边缘化呢?我不了解,因为我没有看,只是我的一个怀疑而已。(未经本人修订)
赵农: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茅老师。
我现在有点时间谈谈我的看法,刚才讲到上访信里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罢免,一个是选举。其实罢免可能和选举本身也有关系。所以,我认为仝博士从海外文献拿过来做,这个有好处,就在于我们探讨过程中有统一的范式,让大家同行之间容易听懂各自的语言。但是也有不同的一面,很可能忽视了我们本身的问题、问题的敏感程度,或者是影响论文而妨碍了抓住要害。
比如我谈这么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的村子是什么?它是一级类似于基层政权,又是一个财产的集体所有者代表,他是两种性质合在一块。让我发现这两种性质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问题,最早来自于2001年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说山西某地老窑头村发生了贿选,其贿选规则是这样的:只要某人当选,就承诺给每个村民若干数额的钱。于是,竞选变成了竞标。谁掏的钱多,谁就当选。最后虽是选出来了村领导,但上级就以贿选名义,宣布这个选举无效。我看了这个新闻节目之后想了很多,这个事情没有结束,我当时就断定,在我们这种公有产权和政权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不能兼顾,这是非常尖锐的。仝博士刚才谈到了道义,所有集体成员要平均分享到这个集体利益,这本身是符合道义的,虽然道义本身还远远不止这点。“实用”的概念其实是想表达“机会主义”的含义,就是当我维护我利益的时候,用得着这个就用这个,用不着这个就用那个。所以,你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缺乏一语道破的东西。
刚才我讲到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不能兼顾,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正常投票投出来的,这便是符合程序正义的,但是也许不符合实体正义。因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贿选实际上是一个租金的提前分配。就是我掌握着集体资产,可能有一部分利润,这个利润如果是我通过正常选举选出来,我来支配这部分企业,可能我们家族的人全部分享这个额外利益,你们分享不到。我若通过贿选方式,即我承诺每个人,见人都有,等于把集体资产租金部分做了提前的平均分配。这是符合实体正义的。这就给出一个难题:你想符合程序正义,就未必符合实体正义。你若符合了实体正义——租金的提前分配和耗散,但又是贿选而丧失程序正义。所以,这种矛盾体让我们中国法治的建设变得异常困难,人们可能在追求公益、正义的过程中,总是没有办法上升到权利和规则层面、法律层面和宪法层面,为什么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争论,都能讲出一番道理。你说我讲规则,我说你规则本来错了,我为什么要坚持规则?那么我们就坚持利益吧。“实用”就是这样而来的。所以,从民事上升到政治的,上升到社会的,这个正义的演化过程就被人为地撕裂了。又如,浙江一个山村,有集体山林,就明确地展开贿选,有一个人掏了200万居然没选上,他自己认了,他说在贿选规则下我没选上,无所谓,我认这个选举结果。为什么?大不了自己的工厂一年白干了。有人是尊重这个的。最差的是哪种人?开始也进行了贿选竞争,但是没选上,没选上之后就告到上级,说对方采取了贿选,对方不应该。刚才我讲到了,一旦贿选符合实体正义的话,你就能理解他最后占据资产,以公谋私,就是合理的。我事前就将资金给你了,我的小舅子管这个企业,这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不能说把钱掏出去了,把集体控制权拿到了,我花了钱你还告我,说我小舅子占了集体企业以公谋私。所以,这就是中国问题非常复杂的一点,这仅仅是我个人观察。我有一个推论,什么推论呢?集体占有资产越多,选举问题越大。如果是一个山村里面没有太多集体资产,可能还好一点。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下面,我们请仝博士给大家的问题做一下回应。
仝志辉:
我今天没有遵守规则,没有准时到,非常道歉。不过我觉得天则的规则也有点问题,因为评论的太多,从时间段上,到我回应隔的时间有点长,如果能及时回应的话,我就可以讲我当时想到的话,但是也不一定可以完全回应。当然这个也怪我,就是在规定时间里面没有充分讲出来。
我对评议的总体印象是,这不仅是想法的交流,可能也是偏好的交流,表现了不同做学问思路的偏好。这种讨论我更多还是理解为了是看了文章以后的讨论,但是天则这个活动确实是公共的,既有讨论也有演讲的成分在里面,我可能对后者看的不是很重。因为这个文章应该是最迟下个月初在《中国乡村研究》发,如果今天我讲的表达不准的话,以那个表达为准。因为那个已经编排了,今天大家的意见不能吸取了,这个非常遗憾,因为大家今天回应里面有很多值得我吸取的地方。
我从一开始说。就是张静老师的四个评论。她第一个评论讲到我说的权利意识论和规则意识论背后有一个遵循的东西,她没有明确说是不是两者都遵循,就是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一个理性化逐步提升的过程,他们甚至于观察这个理性化到了什么程度。她着重看这个变化,我没有把这个明确点明,也没有讨论这个。比如从我感觉到的,可能这个对话深度有问题,或者找的对象有问题。但是,正像他们的争论表现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语言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不断地解释和附加自己的意思。正像刚才吴长青讲到,就是这个权利意识论的标签也是规则意识论贴给他的,我这里其实也是借他们这种争论想探讨中国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抗争意识这个事情,他是实际存在的,我觉得在他们的解说里有可能会歪曲这个东西,我就想讲我的一个观察,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理解他们对他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历史有这样一个预设。
第二,张静老师说上访者的策略性的表达和真实意愿的关系,尤其是当策略性表达也用了主流意识形态,这种表达多大程度上代表他真实意愿?如果说从策略表达中不能分析它真实意愿的话,这是我怀疑的。如果这个问题是说这个材料是不是足够用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可以放到后面回应。
第三,讲到有的国家,就是对第三世界农民政治态度的研究、意识的研究当中也讲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跟我讲的实用道义意识有相像的地方。这个是不是不是中国农民特有的?这个我同意,因为我的文章当中有表达,我说实用道义意识包括斯科特和庇护主义的研究,我觉得都有某种兼容性,但是作为我自己还是自觉的用中文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说对于中国人了解这个事情就够了,至于是不是有一些农民普遍的政治意识,就是我们说这是农民普遍的来佐证中国农民不是稀奇古怪的,这只能起到一个修辞的效果,不一定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至于研究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他如果看中文,他去用这个再讨论他本国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当然他不讨论也没关系。
最后说到我的分析强、资料弱的问题,某种程度我是同意的,我的标题也是说“从理解上访信开始”,这个问题真正要说清楚,真是要把抗争整体过程,以及农民意识在其中的变化,以及各种细节都要说清楚,可能这个问题才能充分展现。这个文章其实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第二,我体会到提出这个问题包含一个建议,就是写法上的修改,但是有的时候,我既然写这么长了,就是在写法的某种表达规则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为那么多信,甚至有人建议我列成表格,刚才大家提到具体事实问题我在文章里面写了,就是多少封信是写什么的,这只是一个习惯,我觉得写法没有高下,最终看这个问题阐述到什么程度,我理解为了更加精细表达还是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第二个我想讲雷弢老师对我的评论,我觉得他提到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农民对现有法律规则不遵从,表现出道义的一面,但是有可能这个规则本身也不是和维护权利的目标直接相合的,就是这个规则本身也有问题。就是完全用这个规则替换权利,这个论证是有瑕疵的。因为我用这么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其实就面临这个疑问,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农民是怎么理解这个制度本身的,以及它的规定的?这是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在表达里面,他的表达,我里面有具体例子,这时候他不把权利说出来,他觉得我利用权利话语,法律规定的都是堂而皇之的,我直接把我的道义理由摆出来,这时候他没有试图比较两者,而就是作为学者的在比较,他们就直接觉得道义就高于法律。他就是这样一个说法,不管法律规定怎么样,你不符合我这边的情况。这样我当然可以认为他是一种道义意识,不是权利意识,即使他错置了对象,这种权利规定也不太对,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不妨碍他不是那么看重权利。
第二,雷老师还讲到,就是我这个实用道义意识和权利意识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个权利意识说的是我在意我的利益,我的实用道义意识也没有推翻这一点,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来说用法律来维护他的利益,实用道义意识是排斥了这点吗?当然没有。我刚才表达确实有不清楚的地方,我说他们不是追求选举权利,而是在意实际经济利益,作为我整个具体论述的开始,然后我说他的政治性没有那么强,不要把权利意识太强调政治权利这一面,还有经济性这个侧面,类型民事权、政治权、社会权的区分,就是他的权利意识不是那么单纯的。这是一个起点,我认可这点。但是,我说这个道义意识成立的根本理由在哪呢?他根本的理由当然不是说我这个,他是说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利,就是我有我自己这一块东西,你不能给我剥夺了,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平等分享共同利益。这是我比较强调的,这个跟他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强调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这里并没有讨论利益和道义的区分,道义和理性也没有对照,没有故意突出抗争是非理性的,没有强调这种道义行动激情的一面,那种非理性的一面。
同时,我很同意雷老师讲到,就是讲这个权利体系,就是马歇尔讲公民权的三个组成,我觉得这种关于权利体系的论述既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同时也是他们历史发展的脉络。就是我们要看到理论是有实际基础的,他虽然现在被作为一个逻辑解说,但是事实上这个历史过程也是存在的,民事权、政治权到社会权这个发展过程也是有的,所以没有抽象的权利,我认为不能抽象的理解这个权利。我们所追求的权利社会也不是基于一个抽象的道理在那儿说,如果要把我这个实用道义意识归到权利意识这个大的框架里来说的话,我可以这样说,我说的是一种“道义权利”,“基于道义的权利”。但是,因为我这里讲抗争意识,我不是说权利的内容,我就可以讲他是实用道义意识,你们讲权利意识,你说他在要求权利的时候是基于本真的权利观,是基于自由秩序下的权利观,我是反对这一点。
吴长青提的意见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他非常具体的切中我这个研究的内容。抗争意识这点,我感谢他点明我把视角从抗争过程中的策略转移到抗争前期和抗争后期,我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工作,而且我在我的文章里面讲到,就是上访信带有某种反思性,尤其是后期访谈的时候更带有某种反思性。因为上访信写的时候,他的抗争已经做了,他在地方层次已经做了,他的合理化是属于在抗争后期的合理化。他为什么抗争?从这个访谈以及他叙述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出当初他为什么要反对这个事情。这里面确实与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这是直接就意识本身来研究意识本身,而不是通过策略去逻辑推演。因为他们说权利意识,他是讲他们在抗争当中用这个法律做依据,然后他们有一些不断的变化,甚至他们到中央层面,他还要求立法。比如说在个人研究的后期,李连江也是承认他是权利意识论者,就是接过对这个变迁的理解,为了推动进一步争论。他就是根据问卷统计。当你去问农民,就是你觉得应不应该选举乡镇长?应不应该直选省长?应不应该直选国家主席的时候?当然相当比例的农民都认为应该选举乡镇长。他把农民这种回答和宪法规定比较,宪法规定现在不能直选乡镇长,不能直选国家主席,这说明农民权利意识增强了,这个权利意识就是针对制定规则本身的权威发出挑战,他不再认为你宪法写的都是对的,我可以提出宪法没有规定的一些权利要求。我认为这个材料当然是很严谨的统计,但是也忽略了问卷本身回答的情境,农民愿意让自己表达的有你学者认为的群体意识,而且这个回答和他的行动没有关系,他就做这样回答。但是如果他在行动中是不是这样想的呢?在实际抗争中,我说的抗争意识的情况下是不是这样想的?他的行动有没有遵循这种意识呢?可能起码强度要弱很多。
第二,他讲到上访信与访谈的偏差,就是说我是在利用这个来讨论问题。我是同意的。但是,他讲到对上访信的利用还没有完全发掘够。怎么更好利用上访信呢?也与对上访本身和上访过程深入理解有关系,这是相互互动的。如果我们单独把这个上访信作为一个材料分析的话,我觉得他是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论域,甚至可以从方法论上好好追究一下。因为我谈的时候也对以往少数几篇利用上访信做分析的文章不满,所以我要认真利用这些上访信。
第三,他讲到研究意识本身非常困难,这个实用道义意识本身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从这个材料里面是不是反应这个?因为我这个也有自己框架的影响,我现在只能做到这样。
第四,他说也是讲权利意识论和规则意识论是不是恰当的对话对象,真正的争执是抗争者正当化自己行动的策略不同,以及他依据的道理不一样。这个道理不应该这么泛化或者固化成抗争意识,因为抗争意识这个词概括的有点大,或者跟对象不是很能对应。其实我的抗争意识包括抗争动机和抗争理由,这两个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捏合在一起。因为曾经有做心理学的跟我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也是想由权利意识开始讨论,因为他们是有现成的说法,有这个词,还有规则意识,也是概括成这个词,我们在中文里面这个意识当然讲主观的层面,也大致能够对应,我没有在用词上做基于更多考虑的区分。
最后他有一些研究建议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讲对上访进一步的研究。我现在想下一步做,就是进入完整的抗争过程,去具体分析。他里面讲到的上访者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意识会有变化,其实会有变化,这个主观层面变化怎么概括呢?如果用道义这个词的话,道义应该解释得更宽泛、更多,我同意。这个里面他讲到以铁肩担道义,吴长青讲的就是“英雄气概”,这是我同意的,就是抗争者群体之间相互激励,以及他们因内部信义而产生的一种意识。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这里的实用道义意识更多是讲的普通村民的抗争意识,他们偶尔会加入这个集体上访,很多时候也会沉默,但是沉默不意味着他没有不满,这种不满我认为也是一种抗争,他跟偶尔出来当面抗争行动这个意识是有连接的,而且本质上是相同的。吴长青讲的“英雄气概”更多是在长期上访者,或者上访精英中表现比较强烈。即使是这种英雄气概,我说的边缘化的时候,也有这种英雄气概不被普通村民理解的,你觉得用道义也可以,我觉得不用也可以,就是用你说的“英雄气概”也是可以的。
然后是张曙光老师讲的。我觉得他对经验本身非常敏锐,就是他提的问题真是非常到位的问题。他讲到对资料的具体分析,因为我自己感到的时间不太能讲那么多,所以没有讲那么具体,我在文章当中确实说他们反应了几类选举问题,各有多少封,然后讲到贿选有几个案例,有什么情况,我都讲了。但是,他提到了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上访信是集体签名还是个人签名会不会有不同?进一步到上访信写作过程,他们到底是集体抗争还是个体抗争,这个表现的抗争意识在上访信表达层面是不是有不同?我觉得在分析上也是应该注意的。
另外,就是对不同权利的追究,比如在贿选这个案例中和针对其他选举违法的抗争中会不会意识有不同?然后,这种被边缘化的上访者,他是不是有一种流氓心态?我们普通讲的话,他可能不是很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他本来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出格行为的,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注意的,而且这个确实需要解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特定历史时期是这些人成为历史推动变化的一种力量。我们在今天的上访者当中,可能也看到这种心态。
还有茅老师,他没有对我文章提问题,但是我同意他的很多说法。
然后是赵农老师讲的,我觉得他讲的问题我是同意他的概括,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不同意。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经验,就是老窑头村的案例我也观察过,我也去村子调查过,而且那个村子出了那个事我最早写了一个评论,我写的是“老窑头村选举的信号”,它那里的这种贿选让外人看起来真是匪夷所思,但是特别符合乡村社会的逻辑。当时我是从制度层面说的,我说这是“后选举时代”的一个信号,就是村民不应该再去追究选举权利了,他们应该追究选了这个人以后对他的监督,为什么用那种非常手段才能把那个人选掉,就是要用给村民钱的手段才能把村民带动起来反对,因为原任村主任自己承包了村的煤矿,低价承包,在煤价上涨的时候,他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按照他的威势,按照正常投票,他可能会被选上,所以反对者就用给村民钱的办法,让百姓把这个人选下去。这个案例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我们太看重了选举,对针对权力的日常监督,村民日常参与议事做的不够。但是,赵农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选举的程序正义,就是当时选举规则不能实现实体正义了,通过贿选当选的当选者起码代表了社区里面的实体正义。如果这样说我同意。但是后面的解释我不同意,赵老师说这个实体正义是租值的提前分配,我觉得村民不是追求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村民不是接受对贿选的处理而是要维护这个贿选的结果,因为后面要撤这个村长的时候,他们都反对,村民认为是民政部直接把这个村长撤了。为什么引发这个呢?原村长投入了竞争,也用贿选规则,他没有选上,他去告了,就是你说的后来浙江案例,你引发的那样的联想。我觉得村民既有提前分配利益的一面,也有道义性的,就是对那个人不满。而后来出来挑战原村主任的这个人,他从品德上、能力上都要比前面那个人好,而且他还提出我当选以后要把这个煤矿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重新承包,所以他当选了,村民在拿钱和选一个得力的人这两方面都是看的。第二面应该是我们看到的实质正义,这是中国社会的实质正义,你刚才用租值提前分配那个解释解释不通。
赵农:
这符合你的概念,平均分配。
仝志辉:
您说的那个恰恰不是实体正义,我觉得民主的程序正义就可以容纳你这个意义上的“实体正义”。因为在浙江瑞安就有一个制度创新,你可以承诺村民发钱,但是要公证,就是到司法局公证,你说你当选以后要给村里修一条路,要给老人发多少钱,对不起,不能允许你在选举现场发。第二,你必须发,你当选以后必须发,你公证过得,不能说空话,这样村民更加愿意参与选举,而且将来如果他不能兑现承诺,可以提起罢免。这样就允许了,只是现场不拿这个钱,当选以后还是要这个钱。
赵农:
还是贿选的。
仝志辉:
不是贿选。老窑头村选举这个事情的具体事实,除了柴静的“村官的价格”的报道,这是《新闻调查》获奖的一期节目,还有后面当地民政局的局长,叫魏荣汉写的报告文学,在《当代》发的,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了单行本,对后续过程也有描述。我调查的也包括后续过程,后来通过发钱当选的人被停职以后,两派发生斗殴,被以贿选为理由撤掉的人,后来又被村民选上村长了,这就表明真正的实质正义还在呈现。
另外,我又不同意你把这里的实质正义一步步解释到上升为宪法层次,因为这个是要分层次的。就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有你说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不匹配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中国的实体正义问题,就是我们的实体正义应该用什么程序保证?而你的想法就是程序是不能怀疑的,程序是大家认可的东西。农村选举的问题恰恰是他们对程序正义的想法比较呆板和单一化,村民自治选举规则不应该全国统一,要规定几种选举办法,让村自治体自主选择,有的村可以一人一票,有的村可以一户一票,有的村可以村民代表投票,适合不同的村,我们村委会选举的程序正义里面没有这个思想,甚至有的学者提出来应该设立全国统一的村民选举日,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恰恰是没有发现具体的实质正义导致的结果。而且我不同意你说的集体的权力越大出的问题越多,那是不是说一个国家选举的话,大国的选举一定是很有问题的了?
赵农:
集体所有制占的利益越大,村集体占有的资源越多,在选举肯定问题越大,这是符合逻辑的。
仝志辉:
在其他民主措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逻辑可以成立。我觉得对权力的选举会不会出现问题与权力大小没有关系,村干部出了问题就要削减他的权利,如果你削到村干部没有权力不能做事了,选举也不能存在了。
赵农:
经济权和政权的合一。
张静:
他说的不是权利的大小,他要说的是公共组织这个角色跟经济组织、经济产的拥有者这个角色不分,如果困在一起,就会导致实质和形式问题的紧张。所以,他想说的是经济组织和公共组织的角色分开的问题,不是权利问题。
仝志辉:
集体组织或者共有财产组织领导人的产生,我觉得也没有排斥选举规则。就是对一个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人的产生,可能也不完全是依靠经理人才市场,可能如果是共同成员选举,可能能产生一个合格的权力,再辅之以其他民主制度。实际上在村级权力层面上不能区分公共组织和经济组织。
我要回应的就是这么多,有的我没有回应,可能是因为有的我没有记清楚。
赵农:
今天非常感谢仝志辉博士给大家这么多启发的演讲,也非常感谢张静教授、雷弢教授和吴长青博士精彩的评论,还有张老师和茅老师的评论,今天的学术活动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