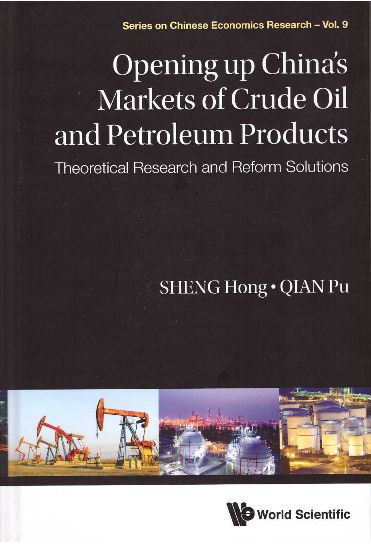同样,梁启超在1902年开始写文章专门分辨了中国儒学的仁政和西方自由之间的区别。因为中国始终觉得比较好的制度就是仁政,西方做得好的也是一种仁政,他认为仁政与自由是不同的。虽然仁政强调保民、牧民,就是褒若赤子,但是统治者仍然权力无限,因此只能论证应当保民,而没有如何能够保民的办法。所以他说“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舌敝唇焦传播其道,非常的辛苦,传播仁政这个观点。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制止两千多年来中国暴君当道,鱼肉人民,就是因为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所以他认为古代提仁政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应当的,是很难得的。但是在现代,他明确说,应该是贵自由,定权限,他认为现在应该放弃仁政的概念。他明确提出来针对现在这一点,贵自由,定权限,定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权限,才能长治久安,“是故言政府与人民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曰,相约而定其界也”,也就是只有两个具有平等地位的人才能够定契约。他认为政府和人民是两个平等的,谁也不能压迫谁,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定一个契约,才能保民。想追求比较好的统治只有这样,他强调政府的地位和人民的地位平等。他说,如果人民的权力是政府所给予的,那么说到底也是政府夺民权,哪怕说这个政府对你再好,但是他说你的权利是我给你的,这也是夺民权,人民的权利不是政府给的,双方定契约。就是说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相对而言,他的思想资源比较陈旧。
但是1902年春天,他也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公民自治篇》,他也强调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在于以民为本,当然,康有为的公民自治谈了很多,因为他游历了那些国家。当然他还是想从儒家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所以《新民丛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前面加了一个序,短短的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就是说赞同这个观点,觉得这只是一个观点,并不代表我们报社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连康有为也是这种观点。这时候梁启超凭借在日本获得了一些知识,写了大量的文章,《霍布士学案》、《斯宾诺沙学案》、《卢梭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就是我们现代的《经济学》),他介绍了很多,可以说他起了重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这时候已经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形成了以革命派和改良派两种政治派别斗争得很激烈,甚至开会的时候冲击、拳脚相加,在报纸上公开地论证,很厉害。他们的论证集中在几个方面:要不要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土地国有等等方面,但是在最根本的方面,比如说要建立一个人民主权、宪政这方面是没有分歧的,大量的文章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是主张君主立宪,一个是主张共和立宪,包括政权的手段。所以革命派也有大量的文章谈到自由、平等、博爱,人类之普通性也,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共性的。他认为国体民生,一切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最浅显的、影响最大的一本就是邹容的《革命军》。他里面有一些话语没有引起重视,我觉得针对现实也很有意义,他说“吾幸夫吾同胞”,我特别为我们的同胞今天与世界列强相遇感到庆幸,因此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文明的政体、文明之革命,幸亏因此我们才知道卢梭的《名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论》(《论法的精神》)、弥勒•约翰的《自由之旅》、《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这是大幸也。他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华夏子孙都应该承继华盛顿的精神。
但是在这一阶段,学理上影响、贡献最大的却是严复,因为他之后翻译了《论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群己权界论》,这是第一次系统地翻译、介绍进来了。严复在翻译中做了许多自己的按语,他的按语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特别谈到自由,中国应该用哪个词来区别liberty和freedom,最后他觉得这个还是很难。他写了一些长的文章,极力把二者区分开。他说,我们现在谈自由,就是指人要争各自的权利,他说人的自由以别人的自由为界,就是群己权界。从历史的角度说,他说贵族统治的时代民对贵族争自由,君主专制的时代是民对君主争自由,在立宪民主的时代君主、贵族都受到法律的束缚,不能任意妄为,争自由就是个人对社会争自由,这时候在宪政社会已经没有君主、贵族欺压人,那么所谓的自由就是个人对社会争自由,也就是个人对社会、个人对国族来争自由,他特别强调要分群己权界,他说任何小事、大事,贵族或者皇上对公民自己的事不该干涉私事,他也是强调公权和私权。他在《政治学讲义》中更加强调这种“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到今日我们就要谈这个了,可以谈这些了。这是真正的治理国家之道”,他说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最重要、最复杂,也就是确立国家、政府对个人管制的权界。他认为在理论上说是很容易,但实际上做又很难,稍微处理得不好就会不得安宁,但是他认为不管怎么样,理论上应该把这个说清楚,所以他就介绍了这些。
分权论确实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基础,尤其严复介绍这些,特别欣赏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法律体系根本不同之处就是西方的法律是公法、私法截然分明,而中国呢,他认为刑宪向来公私不分,公私二律混为一谈。他说一定要把公法、私法从法律上分开。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有立宪,他说,如果说只要有法律就可以说有立宪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中国有立宪,可以说中国的立宪有四千年,但是这个立宪和现代欧洲的立宪是不同的,他说现代的立宪主要是限制君权,而中国古代的法律主要不是限制君权的。严复说,中国古代的立宪,君主可以不遵守,老百姓必须遵守,这是和西方的、和现代的立宪根本不同。他说没有哪个朝代没有法律,所以说如果根据这个就说中国有立宪,那就混淆了古代的法律和现代的立宪的精神。所以他认为中国“本无民权,意非有限君权”,所以他认为现代宪政就是民权,就是统治者必须分权,君主的权力必须得到限制,天子也必须遵从法律。他说,“以此衡之,中国从无宪政”。
在他看来,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的基础的宪政是国家的标志,所以他认为中国没有国,与梁启超一样,说“中国没有国,只是家天下”。中国不是国原话是这样说的,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一朝为之臣之。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王也,此一家之王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因为中国没有分权,由于没有分权,就谈不上是一个国家,一切都由皇帝代表了,那么皇帝一亡,他又是宪法,他认为宪法这三者都由皇帝一人代表了,宪法、国家、王者,都由皇帝代表了,那么这个国家一亡,这个王朝就亡了。他说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统治者死了,法制、法统还在。所以他对孟德斯鸠书中几句话特别赞赏,而且引起他灵感,他写了很多对这句话的评论。孟德斯鸠说“专制之国,国民地位也是平等,但是是民和民之间平等,君主、国家和人民不平等,那么人民就是奴隶,奴隶和奴隶是平等的”。严复说在专制国家中,国民就是一群奴隶,可比喻可数之昆虫。严复对这句话感受特深,他反复对这句话做了阐释,他进一步阐释说,专制制度下,民众间的平等只是奴隶之间的平等,他说“专制之民,已无谓平等者也,一人而外,则皆奴隶。以奴隶相尊,图强颜耳”。他说,管奴隶的那些奴隶,自己实际也是奴隶,尤其他认为,他说“中国之民,犹奴隶也”。
他明确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尖刻,他说中国人民都是奴隶,是斯巴达之奴隶,而非雅典奴隶也。当时我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斯巴达的奴隶和雅典的奴隶,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雅典的奴隶制是什么呢?就是奴隶只有自己的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其他的人——自由民、贵族,无权处置别人的奴隶。如果你处置了,你还要被判刑。斯巴达的奴隶制是什么呢?只要你是奴隶,其他的自由民或者是贵族就可以任意地欺辱你,甚至把你打杀都可以。严复这句话可能说得有点苛刻,说中国人还不是雅典式的奴隶,而是斯巴达式的奴隶,雅典式的奴隶制比斯巴达式的奴隶制还要文明一点,从中是不是又可以得出一个经济学方面的结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私有产权还是比较文明的,就是只要这个奴隶属于我,你就不能任意处罚他。你处罚他,处罚我的财产,要判你的刑。那么斯巴达的奴隶,就认为你是奴隶,就是天下所有奴隶主共有的奴隶,所以奴隶主可以任意地处罚他。因为奴隶制不把奴隶当人,觉得只是个物件,那就强调私有制,两种奴隶制,多说了一句。所以严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就是好的时候,东方的社会,传统社会,确实像父子一般,关系比较好;如果不好的话,就是主奴关系,君有权而民无权。所以西方的是君主立宪,民是权利主体,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他认为,这是国的标准,有国没有国就是以统治者的权力是否受到限制为标志。
那么对于宪政和非宪政这两种政体,怎样判断其高下优劣呢?有人就指出,这是两种是不同的国家形成的不同治理方式,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那种适合西方,这种适合东方,你不能去比较高下。严复提出来是可以比的,他认为西方的是文明之国,关键的是他认为是否有三权分立,刑法议制行政。他有一套论述比较复杂,就是论述分了三权之后国家怎样治理比较好。没有这三权分立,国家往往就暴虐的统治者比较多。所以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的臣民就永远都只是奴仆。臣民只是奴仆,那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有立宪国,官员才可能有辞职、有退出。如果不是立宪国,官员,包括皇帝本人的生命实际上是很难保证的,皇帝可能被推翻,皇帝也可能随时处死某个大臣。他认为,有民权,才可能有官员与人民之间的长治久安。宪政的重要一点是法制,所以严复就特别强调法制。之所以强调,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宪政。宪政就是限定君主权力的,所以他认为中国就是法制。古罗马就有刑、宪、行三者之分,他读到这一段,说那么古的时候就把刑、宪、行三者分立。他说我惊心动魄,西方的国家,罗马那么早就分立了,中国到现在都没有,我们确实就应该把这三者分开。如果三者分不开,也达不到仁政。实际上就回到了我刚才讲的梁启超说过的,仁政和宪政的区别。严复实际上也接触到这个文章,他说,这三权不分立,就很难实行仁政。或者,他并不反对仁政,但是三权分立是达到仁政的一个途径。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并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法律的灵魂就是人人平等,中国的法律特点是以贵治贱。虽然统治者仁可以为父母,但是暴可以为豺狼。实际上就是这种伦理型国家观,仁慈的统治者就像父母一样,但是你赶上一个暴虐的,他就是豺狼。如果圣主顺民可以达到太平盛世,但不能长久,这种制度最后的结果是人民的道德败坏。因为统治者不好,统治者不好,自然人民就不会有好的道德。如果统治者是这样,人民的道德就会败坏,所以他说中国很难逃离一乱一治的历史规律。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到大赦,遇到什么情况国家要大赦,孟德斯鸠是赞成的。严复对这一点不同意,在西方宪政之国可以大赦,但是在没有宪政治国,在仁治之国,大赦就变成了官员或者是皇帝想赦谁赦谁,想关谁关谁,只有实行了宪政。他认为在中国现在,我不同意,就要大赦。他认为这是中国谈到公权、隐私权,他尤其特别警惕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他讲到,“治国之法,为民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便于民。乱国之法,为上而立者也, 故其行也求利于上”,就是说一种法律是为了人民的,另外一种是为了统治者的。他认为,宪政的核心是为国家、政府等公权力划定界限,他最后落实还是在这儿。
他一再强调,公权不能侵犯公权。他以思想、言论自由为例,明确说道,“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就是说思想、言论是不应该由刑法来管的。严复当时就提出来这一点,他谈得很细,他说,“思想言论,消极者之所言也,而非智人所当问也”,就是说思想言论是你说话的人、写文章的人应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统治者应该用刑法、用什么公权力来过问的。严复的这些言论都是非常精彩的。他认为思想言论就属于私的领域,作用不大,最多是个人道德问题,公权力不应当过问,过问就是专制,那这样国民之自由将不复存在。但是,近代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确实强调人民的权利,怎样才叫爱国,但实际上又面临着一个外在的问题,就是国家始终不断地被列强侵略,有几次都差一点所谓的亡国。就是它又要强调爱国,这是一个矛盾,所以严复又想调和这个,他自己又写了要妥善地处理小己与国群的关系。他说,我们国家今天是小己的自由,这方面我觉得他很矛盾,又强调小己,又强调小己要为国群牺牲,要为国家。但是他马上又说了,这个国家由于人民没有权,所以也不能无限地要求人民为了国家牺牲。这种思想很难离开当时的社会、政治,尤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一九零几年正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是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但是你看他思想的基本点,他的侧重还是在这里,人人爱国只能来源于人人享有权利。他特别强调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说,“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至此者,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故民可有拒之之权利,而后才有义务”。他反复地强调,与梁启超最初说的一样,人民有权利了,就是有这个权利,你才有爱国的义务。
最后,他又从强国的角度来论证这个制度的好处。他说,你看西方、日本打开中国,他们都是这种立宪制度,所以你看他翻译的《天演论》,实际上自己做了很多解释,有点曲意了,因为那本书的原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他翻译书名的时候就把“伦理学”去掉了,他谈到了进化论,谈到了弱肉强食,中国人要奋起抗争。实际上,赫胥黎写《进化论与伦理学》实际上是想把“进化论”解释成一种符合道德的伦理,想平衡一下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就是赤裸裸地弱肉强食。严复解释这个的时候,加了自己的解释,自己的侧重。他翻译的时候就把伦理学去掉了,就是《天演论》,这就是“进化论”了,就是弱肉强食,中国必须要起来。所以,他面临着种种的矛盾,最终他还是从国家、强国的角度来谈宪政,所以在当时救亡的语境中,就是所有的思想家不能不考虑到怎样救国,公民自由、小己和群族的关系,所以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引入中国,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脊柱。
实际上,在最开始的时候,在历史情境中,就很难完全撇开救国、救亡。所以当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这种特殊的时候,他接受这种观念,这就是个悖论。如果中国不是亡国灭种,这种东西可能就传不进来,中国人也不会接受它。恰恰就是面临着这种困境,中国人才觉得我就是靠它,接受了它就能使国家强大,这和西方意义上我的原本的立宪的根基就是政府是必要之恶,我必须去来限制它。
这就是说,当你强调个人,强调公权与私权的时候,下面一个阶段就会很自然地强调个人主义,“立个人”。所以,大家看,从梁启超到革命派开始,到严复,特别强调个人主义。梁启超就明确强调,所谓的“开新民”,就是要除却心中之奴隶,“今日预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也”。而梁启超从传统资源中来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接轨,他说,“为我也,利已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令未有不自律而律者也。”他说有要自律才有道德,“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放弃权利也就是没有责任。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基础在于有民权,而民权的巩固在于国民竞争权利,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不肯稍让”,所以他认为中国古代杨朱的“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立者立天下”。他把这个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对接起来,他特别强调杨朱这几句话。实际上杨朱的话更多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这几句话还是和孟子在论争之中留下来的,别人怎样引用他,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从批判的角度,他认为应该重新评价这句话。他说“吸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都认为这句话是最不对的,最恶的,最坏的,最没有道德的,我从前也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认为这句话是对的。这就正好夺了一部分人之权利和全体之权利,“以斯人之权利思想积至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别人就不敢侵犯你的权利。人人都是这样,那就对了。这是梁启超的观点,他当时在日本时是维新派,和革命派论战。革命派的看法也是强调这一点,也是把杨朱的话拿出来论证个人,强调自己的权利。
有篇文章是这样说,“自私自利一念,磅礴郁积人人之脑灵,之心胸,宁为自由死,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之为力也。”西方有人说,“人生之大患,莫不患于不自主而望人之助我,不自立而望人之自立我也。”革命派也是这种观点。在这一点上,二者都是一样的。他们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谈到个人主义、维新派所谓的改良派,都是一样。比如说“个人主义”很多人都诟病这句话,认为是民贼,但是梁启超他们认为这是最正当的话,后来革命派也是这样写的,认为当你强调个人之后,自然而然就和对儒家的疑问提出批评了。所以从那时候,“游学译编”,比如说1903年发表《教育泛论》,就是说什么是教育?教育最根本的一点是贵我,就是个人主义教育,让人人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这是教育的根本。他们认为,孔孟之道,就是儒学在1903、1904年的时候是压制人心的。梁启超也提出来这个观点,认为孔孟之道在那个年代很好,在这个年代不适用了,就是辛亥革命前,大概是1903、1904年。这方面的文章就很多了,他们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以自我为中心。有篇文章明确地提了一个口号,叫“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人类要独立,需要没有圣主,要批判孔孟,这是1904年提的。他们根据这个,好多文章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大成至圣先圣”——孔子,他们根据自然人心论接受了西方自然说,“无心中之理”“理”和“喻”,就好像磁石中的南与北,他就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批判克己礼等等。他们接受了自然人性论,明确地提出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里,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源于习惯,纲常明教是也。他的结论是什么?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中国数千年相传的道德皆伪道德,非真道德也。这是1910年底、1911年初提出来的。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他们非常激烈地批判了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甚至他们比梁启超更进一步。梁启超、严复并不否认仁政,只是认为仁政今天已经不适合了,需要通过宪政,而这些人连仁政本身都否定了,认这那些都是假的,用仁政来统治人,甚至认为孔子为中国文章之江总,束缚人心非常厉害。
这时康有为就认为中国就缺一种信仰,缺一种教派。西方的富强在于武器,武器背后是在他的富,他有商业,商业背后他认是有基督教,康有为认为中国就缺乏这个,他就想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这时候梁启超就公开反驳了,写了几篇文章,康梁师生关系就此公开地决裂。他写了几篇文章具体说现在为什么不能尊孔,认为你把孔作为宗教,容易引起宗教战争。中国已经有信基督教、信佛教、道教,你把那个作为国教,会怎么办?并且他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儒教束缚人心,这是梁启超对康有为已经提出这种批评了。所以我认为以个人权利为代表的契约论国家观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在先进的知识界非常普及了,你看他们谈的都是我们现在还在谈的问题。他们这种契约论国家观实际上我们讲,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明显的、直接的影响。
陈独秀明确说,要问应当不应当爱国,先问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人民的集合,就是梁启超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五四的很多东西只是把梁启超他们用文言文说的变成一种白话文,所以影响更大,包括国家观,包括对孔孟的批判。所以我写过文章很早就论证说,所谓的五四反孔,根本不是自五四开始,到1905年前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已经形成思想界一个很宏大的潮流,只是那时候没有变成白话文,而五四只是把那些话变成了一种白话文,所以我觉得如果赞扬五四的,也不必过于赞扬,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梁启超、严复和后来的一些人都有的;否定五四的也不必说就是从五四这儿开始的,它只是从梁启超那儿开始的,把文言文的变成了一个白话文的。当然,对五四这一代,他们谈到国家观的时候很明显地受到了契约论的影响。比如说刚才陈独秀讲的话,包括五四时期还有一位叫高一涵写道“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也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也有义务。”高一涵说,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立于国家之下,与全体人民受之于国家宪法规条,执行国家义务。他认为人民和政府都是国家之下的一种东西,要国家就是为了谋人民之幸福。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谋人民之幸福,那么这种国家存之也无所荣,亡之也无所惜。高一涵明确说到,我说的爱国的行为就在扩张自己的权利,通过自己的权利在国家之内尽量扩展自己的权利,他说“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国家存立之要素,两败俱伤也。”实际上严复当年说的都是这句话,只是高一涵说得更接近白话一些了。所以我今天基本就讲,从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对现代国家观或者契约论国家的了解,到一批知识分子到日本之后,和最开始徐继畲他们点点滴滴的猜测差别就很大很大了,这时候至少在知识界接受了从传统伦理观,完全是按照契约观来接受了这种国家观,一直到五四还是接受了,包括实际上从梁启超、谭嗣同就提出了。所以我特别写过文章就想说明,反儒的思想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当然,康有为没有。
当然,下一个题目就是说,这种契约论国家观为什么在五四运动达到顶点之后慢慢突然就慢慢被列宁主义的国家观所取代?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