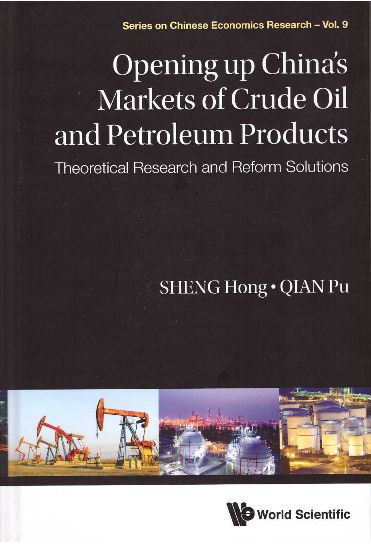张曙光:好,刚才杨继绳先生讲了首先是关于人口数据的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有多种多要样的说法,一般的就是3000万左右,而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那们姓陈的说营养性死亡250,饿死的还是很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本身差距很大。第二,他举了很多当年的案例来分析当年人吃人、打死人、怎样争购、怎样吃食堂造成了死人的现象,特别是讲了如果没有庐山会议,少死2800万。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应该是反左纠左,结果又纠右、反右,所以这个东西就反了,造成的问题就更大了,后来又搞了大跃进,所以搞出来这么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弄清楚。当年人口所是从我们室分出去,成立的人口室,然后再成立的人口所。
这样,我们请了几位关心这方面的专家,下面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些问题怎样看,第一位是王跃生教授。
王跃生:我虽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在关注,但是的确还没有研究,只是谈一些的粗浅的认识。
关于人口损失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口数量变动受三个因素的制约:人口的出生、人口的死亡和人口的迁移流动,但是在一个国家整体地看,我们的迁移流动就不用考虑了,在讲到一个省、一个区域的时候或一个局部的时候就要考虑。在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增减的时候,这个迁移可以忽略。我没有见到这篇文章,就是您刚才说的对人口死亡的低估流动的影响,如果是计算总量的话,这就是一种误区。如果计算流出,那除非是向国外迁移,否则所作解释非常牵强。
现在大家就考虑怎样脱离这个误区,就是说1959年的人口总量和死亡这种人口衰减过程发生之后,比如说1960年或1961年两年的数据做比较,这就进入一个误区了,误区就是说,刚才杨先生也讲到了,就是死亡漏报问题。现在我们还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假如说1959年是6亿7000万,假如当时的数据是低估的,假如应该是6亿9000万,假如1961年降低到6亿4000万,那就是说降幅非常大。但是假如说1961年是6亿4000万,如果漏报的话还保持在6亿5000万的水平的话,损失就体现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误区?因为我觉得可以进行分省区的调查,现在完全可以做到。当时哪些区域人口死亡比较多,到河南的信阳、安徽的一些地区,通过分省、分地区调查把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在减少漏报的情况下人口损失数据搞清楚。就是说由点到面,由一地的人口损失汇集成总量的人口损失,这是一种方法。我看到有些学者也在尝试着这样做。
还有一个问题是,刚才杨先生也做了很多总结,我认为制度性的问题非常突出,像盛洪教授就是搞制度经济学的大家。我认为,其实刚才杨先生都提到了,就是说粮食资源的调配方式,我们已经有大量的例子说明当时不是粮食资源的短缺,或者粮食总量的减产。关于政府征收公粮,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历史上叫做租、庸、调这种方式。在传统社会,政府所征收的为产量的10%,现在(指50年代末)可能是30%,非常高。就是说,这种对粮食资源的高度集中或征调方式是影响农民生存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
再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消费的方式。刚才杨先生也提到了,我们在河北南部搞了一个农村社会变迁下的家庭研究。不仅是在我们解放后,实际上可以说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粮食短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马尔萨斯讲的生活资料短缺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或者说人口压力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如何维持生存的?那实际上就是靠小家庭这种生活单位,尽可能节衣缩食。我们从传统时代的文献中会看到,复合型大家庭这种生活方式相对夫妇为单位的小家庭,对生活资料的浪费程度要高得多。这种家庭是处于家长的高度控制下。在这种家庭中,两个儿子或三个儿子结婚后生育子女数量不同,如老大有三个子女,老二有一个子女,那他就觉得吃亏,分家的愿望非常强烈。我们再讲到食堂制度,就是一种消费方式的变化。这就是说,整体上生活资料短缺的背景下,我们只有以小家庭为生活单位,才有节俭意识,才会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而在食堂这种“大锅饭”方式下,小家庭生活单位被取消了,成为一种比复合型大家庭更大、更松散的“大家庭”,没有人对大家的消费进行控制,就是说消费方式变化导致的粮食短缺,这完全是制度原因。
第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整个救济体系的瘫痪。我们讲在传统时代,一个地方受灾,饥民会大量流散到外地,这是难以掩盖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控制体系不像当时这样严密,从中央一直到下面村党支部控制。传统社会官方的直接管理机构向下只建立于县一级,就是说正式的官方统治就到县一级,保甲组织实际上是民间的管理模式,民众行为所受直接控制较弱。另一方面,灾民流出不仅政府不加限制,而且给予赈济,比如政府开粥厂,提供必要的住所,同时还鼓励富人向过路灾民施粥。从汉代以来,这种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时期,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种体系就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我们说,若当时没有出现粮食减产、自然灾害,我们只能从制度角度来探讨饥荒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损失。
我就说这些,谢谢!
张曙光:好,谢谢王教授!我们请第二位评议人陈子明先生。
陈子明: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谈数据,一个是谈原因。
在数据的问题上,我想虽然有很多官方的和民间的、国内的、外国的这样一些书籍、论文,对于在三年或者五年时间非正常死亡是上千万这个数量级的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也是说1000万以上,或者说1700万,2200万,都是千万级的。最多的,也不过是说四、五千万,千万级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从这些数据公布以来,反对的意见也就那么有数的几篇,除了孙经先以外,其他人的我都逐一看过了,这些文章都是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做文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有问题的,这是无疑的。因为杨先生刚才讲了,那个恒等式不成立,就说明这个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根据当时做人口工作的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评估,这个恒等式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死亡漏报,这一点是根据他们长期工作得出的经验,这也很重要。从杨先生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不是拿全国的数据做文章,而是分省来做,按照分省公布的数据来算,那么死亡漏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所以他计算出来的结果就达到了3000多万。其他很多人如果是分解的,按各省的数据来做的,那么得出的结果也是类似。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出了县志,虽然没有普及化,全国3000多个县级单位没有都出书,但是已经出书的这些单位明确地公布了非正常死亡的这些数据加起来也远远不止所谓的250万。现在数据很充分的,只是信阳一个地区100万,很难有人能够否认的。那么全国其它地方加起来才150万?按照一般人的常识和逻辑那是说不通的。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说,县志、市志这些数据还是有漏报的。
我说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就不说了,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是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在80年代用一些方法获得了100多个县的原始资料、原始档案,他全部复印了,这100多个县的原始资料,他拿出了几个县,现在已经在博客和书籍上公布了,都远远多于正式公布出来的那些数字。这100多个县的原始资料如果都能出书,就能使我们在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些原始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检讨,包括下级给上级,就是县级给市级、省级的报告,包括大队给公社、公社给县的报告。我去他的储藏室看过,非常丰富的材料。但是我想说,很可惜,由于他想把这些数据电子化,想带到香港去,这些材料已经在不久前被国家安全局抄没了,而且这个朋友处于取保候审,可能要蹲监牢的悲剧。那么就是说,这些数据不是没有,就在全国的档案局里,只是你肯不肯拿出来给大家、给学者看的问题。只要你下一个命令说可以,很快真相就会大白。
我记得廖伯康在他的文章中讲,当年,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保险柜里的小本本有很详尽的数据,他冒死到北京来说,四川非正常死亡1000多万。结果杨尚昆拿出这个小本本一看,基本和他所报的数据吻合。所以他说,只要把杨尚昆那个小本本拿出来,给大家报一下,好多问题也解决了。所以现在说250万,说什么往一个两个数量级上减的人,应该说不是太无知,就是太无耻。这样的东西原来只在网络上出现,现在竟然上了杂志,上了报纸。可以说,眼下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比10年前、20年前更加无耻了!真是一个让人惊骇的事情了。
第二,我想说原因。实际上杨继绳先生这本书已经透露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期待着将来能够有一本与《墓碑》一样的书出现,这就是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打死人,打死人是饿死人的原因。实际上杨先生的书里关于打死人零散的数据也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还缺乏一本全国性的数据。我这里说的打死人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在政治上把人打死,一个含义是在肉体上把人打死。政治上把人打死也很厉害,当然政治上打死人的一个后果就是也被打死、饿死,比如说储安平,先在政治上打死,后来在肉体上也消失了。1957年判了,到底是50万右派,还是几百万右派,估计现在还是一个不清楚的数据。1958年还有一个补打右派,又是多少万。我过去看的数据是说1959年反右倾,官方的数据是300万,但是刚才我在字幕上看是近1000万,邓小平说的。这些政治上被打是后来饿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被打的都是高层、精英,在底层就直接肉体上打死了。刚才说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数据就是一个县为了逼所谓的“瞒产”就可以打死1万人。那么,我想了解,在全国,在所谓“瞒产”问题上,包括在赶老百姓上山、砍树、炼木炭、炼铁,几千万人上阵,要把他们驱赶出家门的时候,打死了多少人?在整个1958年到1962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打死了多少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尚需要研究和公布的数据。我斗胆地说一声,这种数据也应该是百万数量级的。这个百万数量级是导致千万数量级饿死的最直接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老百姓不会屈服,地方和社区精英也不会屈服,包括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干部也不会轻易屈服。但他们现在政治上被打死了,又在肉体上被打死了,使得那些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不可能再去抵抗了,这直接导致后来几千万人饿死。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应该有人把这个打死人的全过程和统计写成一本书,这本书也会和杨继绳先生这本书一样流传不朽。我就说这些,谢谢!
张曙光:好,谢谢陈子明先生!下面我们有请第三位评议人——石秀印教授。
石秀印:非常感谢杨继绳先生!我不是做人口学的,也没有数据,但是我有两个希望和建议,就是说一个数据就是死了多少人是不是能有一个分类呢?比如说有确实直接饿死的,也有因为间接病死的,刚才您说也有打死的,另外是不是还有因为治安案件死的,能不能有一个差别性的分类。
我想有人说这个数据是250万,有人说380万,当然有一个主观动机问题,也有一个是统计口径是不是有问题。你说饿死是一种什么样的饿死。这是第一个,就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我们才能把这个数据对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杨继绳先生是搞社会分层的,你有没有一个数据来证明死的都是什么人?是普通农民,是中农、贫农还是地主?你说还有城市的什么人,能不能有一个分层?我认为这对于说明情况也是很意义的。
第三,对原因的解释,因为这一段我是在做一个研究,就是中国国民的特点,中国国民性问题研究,也可以充分说明我对你的研究的观点。中国国民性是什么呢?其实回忆饿死人的背景,就是1957年的背景,实际上1956年、1957年,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我记得还清楚的话,那时候共产党要整风。共产党整风要整什么风呢?是三种风,一种是主观主义,一种是官僚主义,一种是宗派主义。也可能我记得不清楚,就因为整风,请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就出现了右派,就开始反右。那么实际上这三种风,我认为是后来大饥荒、大跃进、后来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是主观主义,什么叫主观主义呢?实际上用哲学观点来讲,就是唯意志论,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不用遵照什么规律,也不要遵照什么规则。第二个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表现很多,但是最初的表现就是上级对下级的压制、不关心,包括我们现在的腐败也好、不作为也好、乱作为也好,我想那时候可能都会归入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加到一起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唯意志论,官越大,我想做什么我就要做。
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合作社,合作社到80年代就解体了,为什么解体了?不符合规律。但是我们觉得那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之后,大炼钢铁也是这样,然后斗右派也是这样,办食堂还是这样。就是说,只要我有了权力,我在上面,我想做什么这个事一定是对的,一定能够做成,一定会为老百姓谋幸福。
我认为唯意志论也好,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也好,一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人口在1959年、1962的时候大大地减少,减少了3000万。我记得秦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回顾中国的历史。根据他的观点,中国历史上人口就是大幅度地跳动。某一个朝代中兴了,人口逐年发展,然后过了一段,人口逐渐减少,几百万、几千万都是,都是这样波动着过来的。这样来回忆或者联系的话,我们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现象,也是同样的一个主因在起作用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或者深究的问题。实际上1959年以后,俄国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突发或者偶然的事件,它是不是与我们常说的中国历史循环有关系呢?我认为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到现在,就是说主观主义也好,官僚主义也好,宗派主义也好,消失了吗?我们现在的有些政策真是依照市场规律、客观规律、世界的一些普遍的规律来制定的吗?这个事我再联系到钱学森和李约瑟。李约瑟有个难题,钱学森有个专题,就是说,李约瑟说为什么说到16世纪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就滞后了呢?钱学森说为什么我们不出人才呢?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唯意志论的价格的话,我们想到什么做什么,那我们还尊重客观规律吗?我们还探讨客观规律吗?我们制定政策还尊重规律、探讨规律吗?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且与我们的民族性、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张曙光:好,谢谢!我简单讲两点。
第一点,我认为制度方面的原因都是对的,确实三年饥荒是人祸,都没有天灾。三年是正常的年份,完全是人祸。在人祸里面,大家讲的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我们没有很重视的,就是修食堂、征购,这些从公的方面让人饿死的状况,另一面就是大炼钢铁、兴修水利,那种大强度的劳动让人们体力消耗得那么多了,然后又吃不上,所以这三年的事情才有这么严重。所以我认为几千万人上山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的两面,恐怕这一点还要研究。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过多的支出和过少的营养,必然是这样。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城里死的人少呢?我认为城里最重要的是浮肿。当时茅老师20岁上大学,腿上一按一个坑,好长时间起不来。就这种状况,浮肿,每天还有三顿饭,尽管那个饭,下午的饭一个大锅,倒进去的稀面条,提前两个小时就倒进去了,一泡,那种状况。我觉得有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看,就是顾准的《商城日记》,记述了每一天谁家死了人,谁的什么亲人死了,人吃人怎么回事?我认为不仅这些情况,而且从饥荒理论来看,顾准的《商城日记》饥荒理论的所有要素都在里面。我把饥荒理论,他讲了三个要素,一个就是公安户口管了,粮食管了,第二条,人民公社,下来就是公共食堂。粮食不够、高强度的劳动是一个用新的办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马尔萨斯。大家去看,他把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弄了一个叫糊口经济,就是打的东西只够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又把粮食拿走了,又高强度的劳动的,人口死亡的状况是一个必然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如果是民主体制,没这个问题的,信息就可以披露出来。咱们的信息可以披露出来吗?你现在知道死几千万人,你那个时候知道吗?他把信息首先封闭了,而且这种统治只报喜不报忧。死了人也不报,报了受批评。既然如此,上面也想听好话,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那一种状况,下面谁敢说吗?恐怕谁说谁就要往枪口上撞,首先要被逼死了。所以既然这样,你想一想死人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状况了,大量的死人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今天《社会科学报》上这样的文章,我想这样的人怎样去想?就是刚才说的,仅仅信阳就死了100多万人,而且这是中央自己下去弄上来的数字嘛。信阳是一个专区,河南有多少个信阳专区?河南是一个死人重灾区,贵州也是,就是食堂办得好的都是死人最多的地方。河南办得好,贵州办得好,死人最多。所以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恐怕需要很好地去研究,制度的问题能解决不会发生饥荒的,当时不是粮食减产,就是减产的情况下,也不会,对不对?过去还有饥荒开粥棚的,毛泽东自己也受过粥棚的救济,我们后来能开吗?你见哪个地方开了?所以我认为恐怕历史上的事情绝对不是,就是皇权专制的情况下也没有像我们60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总结的事情,后代不应该忘记的事情。现在还把这个事情包起来,让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讲起来似乎是荒唐的事。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杨老师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关键是你的书大家看不到,只能在网上搜到,出版的书是进不来的。我认为这些历史的东西需要去看一看,需要去看一看真实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如果忘记了历史,恐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嘛,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是要重视历史。
我再说一点,我认为大家可以看到,杨老师今天讲的东西都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学问的典范。不管现在的数据准不准,他多种途径、多种办法来,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来算,为这个事情,他去各地去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到信阳专区去,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调查,才有这样的东西,这才是真正扎扎实实有学问的东西,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来学习。这是从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可以从杨老师身上学习的东西。
我就讲这样两点,下面请杨继绳来做回应,回答大家的问题。
杨继绳:
刚才一位学者让我说一说什么叫“饿死”?网上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用人体的能量平衡来解释。为了搞清人在饿死过程中的生理机制,我多次请教天津医科大学王梅松教授,并在他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几本医学著作。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间。按当时全国粮食平均供应量换算,当时中国农民平均每天吸收的能量只有600多千卡。能量入不敷出,只能“消化”自己的身体。体内储存的“糖原”可以维持一天,然后分解脂肪,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对自身的分解是一个残酷的生理过程。例如,完全依靠分解脂肪产生热量,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心肌萎缩就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萎缩和功能低下,会产生种种疾病。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进一步减少能量的吸收。人体内的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抗体和免疫蛋白都是蛋白质组成的,没有这些,各种疾病就会随时发生。也就是说,人体在自我分解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诱发疾病而死亡。《墓碑》“粮食问题”一章的“农民的热量平衡”一节里,介绍了因饥饿而死亡的生理过程,用生理学知识回答了什么叫“饿死”的问题。为了否定大量饿死人这个历史事实,孙经先等人还生造了“营养性死亡”的概念。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什么叫“营养性死亡”?什么叫“完全性饥饿死亡”?喜欢玩弄概念的孙经先,没有给他的新创造作出科学界定。孙经先说的“营养性死亡”,是不是指我刚才说的热量平衡这个过程?如果是的话,“营养性死亡”就是因饥饿而死亡,绝不是营养过剩、营养不当而死亡。
刚才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问我怎么看。
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邓小平的贡献就是搞经济改革,只搞经改,不搞政改,改革的结果是权力市场经济。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这个制度。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既误读了资本主义,又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我觉得还是用“权力市场经济”更好一些。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和没权的不公平,成了社会的两极。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不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只能靠警察来维稳。但不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越维越不稳。现在,当局一方面想在经济上继续改革,扩大开放,这是好事,当然有外部压力,不得不搞对外开放,加大开放力度。另一方面,政治上大踏步地倒退,回到邓小平时代以前了。邓小平因为只搞经改,不搞政改,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现在经济改革前进,政治上大踏步地倒退,这不是使问题更加严重了吗?矛盾更加激化了吗?所以我非常忧虑。知识分子都应该说话,用我们嘴巴说话,用我们的笔说话。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谢谢大家!
张曙光:好,其实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两篇文章我还想不到,正因为看了这两篇文章,所以我才觉得要讨论。所以其实反面的东西也有好的一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更深一些,不要藏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毒草也有好处。
今天下午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杨继绳的报告很好,大家的评议虽然还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也很正常,还是可以展开讨论的。我们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平台,所以各种各样的话都可以讲的。今天谢谢杨继绳,谢谢几位评议人,谢谢参加会议讨论的人,谢谢大家!